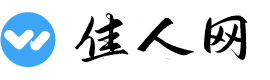人们常把《孙子兵法》称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兵书。严格来说,这种描述是不正确的。在《孙子兵法》出版之前,中国古代不止有一本兵书。但这些兵书古籍由于思想比较浅薄,特别是文字不优美,波涛汹涌,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不合时宜。《孙子兵法》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兵法。明代毛袁遗说:“前有孙儿,后无孙儿。”意思是《孙子兵法》之前的兵书精华,已经被《孙子兵法》捕捉吸收,无一遗漏。这也说明《孙子兵法》中的兵学成就是在继承前人兵学思想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考察前孙子时代的军事文化,不能不回到“古司马兵法”。《唐太宗·李·龚伟问右》指出:“这个世界上有四种类型的兵家,战术、形势、阴阳、技巧,都发表在司马法上。”显然,《古司马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总源头,也是最早的军事文化的系统载体。
西周时期,文献典籍“官存世,民不存”。当时的军事典籍由官方编撰,专职授课。这类文献一般称为《司马氏兵法》,也就是司马芝官方用兵法典的总称。作为一个类名,并不是具体引用某一部军事典籍。先秦时期所有的官方军事文献(法律、法规、规章)都属于古代司马氏兵法,如《左传》引的《君之》和《孙子兵法》引的《郑钧》,都是古代司马氏兵法范畴下的军事专著。汉代时,人们仍能看到一些零散的资料,惊叹其军事理论原理、阵型战术要点、训练编制大纲的丰富和深刻:“读司马法,影响深远。三代征服者虽未能体悟其意,如其文,但甚少称赞。”(《史记·司马相列传》)此版《司马法》是一部与“古司马兵法”相关的军事思想集。《古司马兵法》最显著的特点是体现了西周礼乐文明中的“军礼”传统,即所谓“争德”。用汉代班固的话来说就是:“司马法是唐舞授意助人为乐、仁义礼行的遗风。”(韩曙《文艺志》)这体现在战争的目的上,强调规则意识和底线,“为义而战,而非为利”。如果非要诉诸战争作为最后手段,也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原则,进行公平合理的对抗,即所谓“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强调“犯反人民罪”和“行不义”,采用所谓“九伐法”:“九伐法强国,弱冯寡,恶人贤害民,陵内有暴则断坛;野荒人散,不服者侵;杀亲者为义,杀君者为残。(见《李周下关马达》、《司马法仁本》)并将此原理上升到“仁义”的层面加以肯定:“古人以仁为本,以义为治。如果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你会得到权力。权力来自战争,而不是来自中间人。所以杀人是安全的,也是可以被杀的;攻其国,爱其民,攻其国;以战止战,虽可战。"发动战争有很多道德禁忌,包括不能趁人之危,不准违反农时,使人受苦,不能在严冬或酷暑这样的季节发动战争等等:“作战之道:不违时,不经人之病,所以爱我民;不加丧,不要凶,所以爱老公,爱人民。夏天,我很沮丧,所以我同时爱着人们。国虽大好战,必亡。虽然世界是安全的,但忘记战争将是危险的。”(司马法仁本)在具体的战场对抗过程中,要尊重对手,遵循光明磊落的原则,进退有度,打仗讲礼仪,杜绝欺软怕硬的行为,摒弃唯利是图的做法:“古人一步一个脚印,只跑百步,三次不放弃,是礼貌;你不穷,就不能可怜伤病员,才能知道它的意义。鼓由柱子组成,以示其信仰。正义不争利,以明其义。能够放弃就是勇敢;末知始,是知其智。”(《司马法仁本》)同书《天子之义》也有类似的主张:“古人相距不远,却不能等。不远则难诱,不远则难陷。”“不要冲,不要开,不要冲,不要超越名单...迟不为诫。”但《楚梁五年殷公列传》言简意赅地概括为:“不逾时伐,不追战,不补服。”同时禁止在战场对抗中实施偷袭等阴险毒辣的战术。比如司马法里的小品强调:“不干车,不自拍。”(引自郑玄《判官李周》)不准冒犯敌国君主之车,也不准从背后攻击敌人。《左传·温柱安公十二年》也说:“若有遗患,弃而不收,无益于你。不要等了,瘦子有危险,没有勇气。”“君子不重伤,不鸟不惜二毛,古之军也,不为噎也。吾国虽亡,吾不能不鼓而列!”(《左传·Xi公四年》)战场纪律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优待俘虏,救死扶伤,禁止报复。是执行战场纪律中的必要含义:“冢和关白告诉军队,‘当你们进入罪人之地时,将不会有暴力的神,不会有野外狩猎,不会有土壤破坏,不会有烧毁的墙屋,不会有砍伐树木,不会有带走六头动物,玉米和装备。看他们老少,不要伤害他们。如果你遇到一个强壮的男人,不要和他对抗。如果敌人受伤了,药就会被退回。" "(司马法人本)在战后善后问题上,不允许战胜方消灭敌人,除恶务尽。而是在确保胜利的前提下,保住对手的生存机会,让他维持自己的血脉:“刑有罪后,王公纠其国,复其位。”(司马法仁本)伐周成功后,任用之子武庚,以商朝之血继续祭天,就是一例。周平定了武庚与“三监”的叛乱后,仍要依靠的普通兄弟魏子作封建诸侯,国号为宋,以继续保持殷商血脉世代相传。宋国的情况并非个案。郑庄公复许与楚国复陈蔡之独立都是相似的。以《左传》为鉴,信而签之。例如,鲁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楚伯即位,封陈和蔡,都被恢复,以礼相待。鲁之子,隐之长子,属蔡,李也,哀吴之长子,属陈,李也”。
古代司马法“争德”的属性,决定了宋襄公在后世眼中的“笨猪般的仁”会被推崇,甚至夸张到“文王之战”的地步:《公羊传》说:“君子傲如鼓,大事不忘大礼。有君无臣。虽然我以为文王之战无非如此。”(《杨公公四年传》)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也以同样的方式称赞宋襄公:“项公在行仁义之时,想当盟主...襄公败于洪,君子以为过,伤中国之礼不足。称赞它,宋湘有礼貌。”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古司马兵法》这种“争德”的属性。这种现象的存在,首先是由战争本身的物质条件决定的,受到现实的制约,而不是道德的崇高追求。例如卦中的“六四”云:“学左,则不咎。”这只是一个符合战斗实践规律的单兵战术动作。它的原意是:在战场上,位于左侧或驻扎在左侧是安全的。原因很简单。手的功能通常以右手为主,左手为辅。毕竟左撇子是少数。冷兵器时代,士兵通常左手持盾防御,右手持刃攻击。所以在与敌人生死搏斗时,尤其是狭路相逢,自然要靠近左侧,迫使敌人在他的右侧,这样就可以用右手杀死他。显然,“二师无咎”原则是古代士兵有意识或无意识运用具体作战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同理,在殷商、西周、春秋初期密集的方阵作战背景下,“不下于六步七步,而只是止。“四、五、六、七”的战术决定了战场行动只能是“相距不远,不及他人快”,只能是“列队行进,击鼓呐喊”。它被赋予了道德元素,应该被后人自觉地粉饰和依附。
其实当时战争的残酷才是历史最大的真相。《丁羽》有云:“不缺长寿。”无论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牙牙学语的蹒跚学步的孩子,都是被宰被杀。然而,周公东征中的“选举实践”也暴露出其残酷性和悲剧性。“那些实践它的人,他们也赢得了它。意思是杀其身,执其家,守其宫。”(《商·成淑·王政传》)可见,《古司马兵法》所体现的“军礼”精神,只适用于夏季中原诸国,不包括蛮夷。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服华”。相反,四夷的那些少数部落,不属于军礼的适用对象,所以说“刑是欺四夷”(《左传》公二十五年)。“晋中木子之行无止境,狄玉之团在大源...不老不瘦,大败。”(《左广告》)是一种服务。晋国在易帝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地位时就攻打了他,打败了易帝。明显违背了军礼中“纵队行进,击鼓”的原则。
即使中原各国遵循了《古司马兵法》所提倡的“军礼”原则,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在战场上,“伤君有罚”就是“军礼”的标准之一。在楚谨鄢陵之战中,你见到子楚时,不得不“避腹顺风”,虽然你一直遵守“军礼”。然而,干露,他也是晋军的将军,致力于杀死敌人的君主。詹志曰:‘姬姓,日也;另一个姓,叶月,将是楚王。如果你射中了它,又掉回泥里,你就会死。“还有,枪毙共王仲穆。”(《左传·成功十六年》)不仅如此,在同一个人身上,他对“军礼”的遵从往往是有选择性的,表现往往是前后不一,完全不同的。作为一个男人,当他在炎陵之战的战场上相遇时,他尽最大努力向郑伯、子楚等敌国君主表示敬意和尊敬。但在鄢陵之战前夕的战略建议中,却主张在楚汉之战尚未定案之前就发动进攻,这显然违背了“无瘦人之危”的“军礼”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理想和现实往往是脱节的。军事科学的概念是一回事,战争的实践又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古司马兵法”所倡导的军礼原则,说到底只是一种道德诉求,而非强制性规定。因此,对《古司马兵法》中的“争德”属性要有辩证的认识。不应该轻易否定,也不应该被后儒家牵着鼻子走,盲从。